我53岁,大侄子结婚我随礼2000块,75岁老母亲嫌少,到处说我抠门
离家的礼
"黄家海,你可真行啊!大侄子结婚就随两千块,你是有多抠门?"母亲颤抖的声音在热闹的饭桌上格外刺耳,亲戚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。
那是正月十五,侄子王建业的婚宴上。北方的冬天,窗外白雪皑皑,松花江已结冰三尺厚。屋内挤满了人,墙角的砖炉烧得通红,暖气扑面而来。
二十几口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,筷子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母亲七十五岁了,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绣花棉袄,是她最爱的一件,已经穿了十多年。袖口和领子都有些磨白了,但还是被她洗得干干净净。
"妈,您别这样。"我声音低沉,尴尬地看着周围的亲戚,他们有的埋头扒饭,有的交头接耳。
"怎么就不能这样?你二哥家都随了五千,你堂弟家随了三千,就你这个当叔叔的,才给两千!咱家又不是养不起你,怎么这么抠搜?"母亲气得手指发抖,茶碗里的水都晃出来了。
我沉默不语。五十三岁的男人,头发已经花白大半,脸上的皱纹也一年比一年深。眼角的鱼尾纹里藏着这些年的苦与乐,额头上的沟壑记录着生活的艰辛。
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,我被迫下岗,那时候多少同事放不下面子,宁可饿着也不去摆地摊。我却什么都干过,发过传单,看过工地,开过黑车,就是为了养家糊口。
后来靠着年轻时学的手艺,在城郊开了个小修理铺,修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,什么能赚钱修什么。一把改锥、一把钳子,几乎就是全部家当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但总算有了固定收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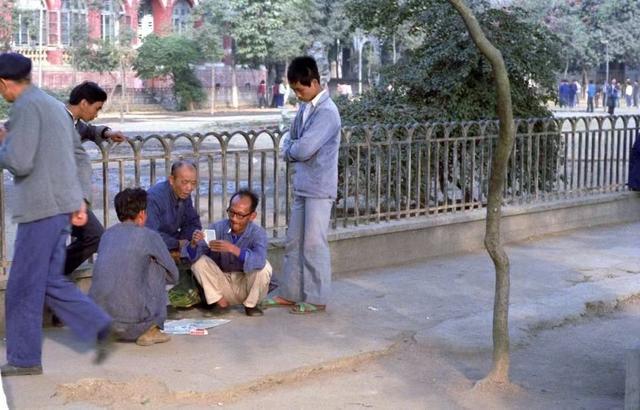
女儿今年大三,在省城上大学,每学期的学费加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些年,我和妻子省吃俭用,就是为了给女儿攒钱。孩子从小争气,没让我们操心,眼看着就要毕业了,我这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。
饭桌上的气氛凝固了。我低头喝了口酒,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,却无法冲淡心头的苦涩。
"老黄,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,侄子结婚就随两千?现在是啥年头了?"二舅家的李大海在一旁添油加醋,他一直看我不顺眼。
当年我和他女儿处对象没成,他就记恨上我了。那时我刚从技校毕业,手里没钱,买不起他要求的彩电和缝纫机,亲事就吹了。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王淑芬,反倒是一场福气。
"就是,现在什么行情啊,两千块钱能干啥?连个像样的电视机都买不着。"又有人跟着起哄。
我放下筷子,看向母亲:"妈,您知道我家什么情况。"
"我知道什么情况?我就知道你女儿上大学花钱,难道建业不是您亲孙子?他结婚您老人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添置!"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这话如同一把刀插进我心里。不是不愿意,而是真的拿不出来。上个月,女儿学校组织出国交流,是千载难逢的机会,我硬是借了亲戚几千块凑齐费用,至今没还上。
我清楚地记得,那天晚上妻子坐在煤油灯下,一针一线地缝补我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衣,说:"老黄,咱们省点,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。"
"行了,别说了。"建业媳妇小声劝着,她叫张丽娟,是县医院的护士,长得清秀,说话轻声细语,很有教养。

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闷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,建业大学毕业那年,母亲生了一场大病,住院半个月,医药费将近八千。当时我在外地出差,是建业垫付了全部费用,还天天去医院照顾。
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:难道母亲对建业的特别看重,与这有关?
想到这里,我抬头看了母亲一眼,只见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自责和心疼,眼角有泪光闪动。那一瞬间,我仿佛明白了什么,心中翻涌起复杂的情绪。
记得建业小时候,他十岁生日那年,老厂里刚刚发了年终奖,我省下一半,给他买了辆"永久"牌自行车,那可是当时最时髦的礼物,厂里没几个孩子有。
那天,建业骑着车在院子里转来转去,铃铛清脆地响着,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街坊邻居的孩子都围着他转,羡慕得不得了。那时候,我还在国企上班,日子虽然不算富裕,但也过得踏实。
我们那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,单位分了房子,虽然只有五十多平米,但胜在安稳。夏天,大院里的人都搬着小板凳出来乘凉,收音机里放着评弹,大人们聊天,孩子们追逐打闹,日子过得舒心。
谁能想到后来的变故?厂子不行了,欠了一屁股债,职工发不出工资。我们这些人从早忙到晚,换来的却是一张张白条。后来干脆宣布改制,能分得几个月工资就算不错了。
四十多岁的人,突然被丢到社会上,四处碰壁。那段日子,我看着昔日的工友有的卖血,有的上吊,心里难受得要命。但我咬牙挺过来了,靠着年轻时学的那一手修理技术,在城郊开了个小铺子,一干就是十多年。

妻子王淑芬在小区当清洁工,每天天不亮就出门,扫地、擦楼道、倒垃圾,风里来雨里去,从不叫苦。回家还要洗衣做饭,缝缝补补,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。
我们省吃俭用,就为了给女儿攒学费。家里的家具都是老式的,电视机还是那种小屏幕的,都用了十几年。但我们从不在女儿面前提这些,只希望她能无忧无虑地学习。
"我出去透透气。"我站起身,不顾妻子的挽留,推门而出。
外面下起了小雨,初春的雨丝细密如针,打在脸上生疼。我摸出皱巴巴的烟盒,抖出一支皱巴巴的烟,在屋檐下点燃。火光在雨幕中明明灭灭,就像我此刻复杂的心情。
当年那个把儿子举过头顶的壮小伙,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。岁月不饶人,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但我从不埋怨,只是默默地扛着。
我漫无目的地走着,不知不觉来到了父亲的坟前。小雨淅沥,墓碑上的照片被雨水打湿,但父亲的笑容依然清晰。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,当年他因病早退,我用全部积蓄给他治病,最终还是没留住人。
父亲生前是厂里的老师傅,一辈子兢兢业业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他常教导我:"人这辈子,不在乎有多少钱,关键要活得有骨气。"
"爸,您在上面看着呢,我真的尽力了。"我蹲下身,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流下面颊。多想听听父亲的教诲,多想在他肩上靠一靠。

雨越下越大,我的衣服都湿透了,却不想动。
这时,远处传来脚步声。我回头一看,是妻子打着伞来了。
"老黄,你发什么疯呢?这么大雨,感冒了怎么办?"她责备的话语里满是关切。
我站起身,淑芬把伞往我这边倾斜,自己却淋湿了半边身子。这个女人,跟了我二十多年,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。
"淑芬,对不起,让你受苦了。"我哽咽着说。
"说啥傻话呢!咱们家里人,还用这么客气吗?"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,"回家吧,别冻着。"
回到家已是深夜,淑芬给我倒了杯热茶,又拿来干毛巾让我擦头发。屋里很安静,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"老黄,给,你看看咱们这些年的存折。"她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,递给我。
那薄薄的存折上记录着我们这些年的艰辛:女儿的学费、生活费,家里的柴米油盐,每一分钱都有去处。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多,但每个月总能存下一点。最后一页上,还有前不久借出去的那笔钱,五千整。
"淑芬,我不是小气,我是真的......"话没说完,喉咙哽咽。
"我知道,我都知道。"她握住我的手,"你妈那么说,不是真的怪你,是心疼建业。毕竟当年他帮了大忙。"
我点点头:"我明白,只是......"
"只是啥?咱们不富裕,但问心无愧。"淑芬坚定地说,"明天我跟你去趟建业家,把话说清楚。"
第二天清晨,门铃响起。开门后,是建业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个盒子。

"小叔,我来看您。"他不好意思地笑着,身后还站着他的新婚妻子丽娟。
"进来坐。"我侧身让他们进来。
"小叔,嫂子,昨天的事真不好意思。"丽娟一进门就道歉,"建业昨晚回家就跟我说了,我俩今天特意来给您赔不是。"
建业接过话头:"小叔,奶奶年纪大了,您别往心里去。您对我的好,我都记着呢。"
他说着,打开手里的盒子,里面是一个陈旧的自行车铃铛,就是当年那辆"永久"车上的。
"那辆车骑了好多年,后来上大学了才换了新的。但这个铃铛我一直留着,声音特别清脆,想起来就想起小时候您带我去游乐园的日子。"
我的眼眶湿润了,接过那个已经有些锈迹的铃铛。我轻轻摇了摇,叮铃铃的声音勾起了往日的回忆。那时候,建业还小,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,兴奋地按着铃铛,笑声爽朗。
"那时候想着等我工作了,一定要好好孝敬您和奶奶。"建业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,"没想到工作后才发现,赚钱真不容易。"
建业大学毕业后在县医院做护工,后来通过考试转为正式工。工资不高,但胜在稳定。
"小叔,这两年我存了点钱,打算给奶奶买个助听器。她老人家耳朵不好使了,看电视总是开得很大声,邻居都有意见。"建业说。
"是啊,叔叔,老人家年纪大了,要多关心。"丽娟在一旁补充,"我们医院刚进了一批进口助听器,效果特别好。"
我点点头,心里暖暖的。也许,母亲并不是真的嫌我随的礼少,而是觉得我这些年很少回家看她,心里委屈罢了。

"对了,小叔,这是我和丽娟的结婚照,您看看。"建业从包里拿出一个相册。
翻开相册,第一页就是他们的婚纱照,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再往后翻,是婚礼现场的照片,亲朋好友的笑脸,热闹的场景。
突然,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:母亲坐在主桌上,笑得合不拢嘴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笑得这么开心了。
照片角落里,我看到了自己的背影,孤零零地站在一旁,与热闹的场景格格不入。那一刻,我才意识到,这些年的忙碌,让我与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
"小叔,您怎么了?"建业关切地问。
我摇摇头,合上相册:"没事,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"
淑芬端来热茶和点心,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很多。建业说起他们的新房,是单位分的,虽然小了点,但收拾得很温馨。丽娟说起工作中的趣事,语气中透着对未来的憧憬。
看着这对年轻人,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。那时候,我和淑芬也是这样,满怀希望地谈论未来,规划着简单而美好的生活。
"对了,小叔,下个月是奶奶的生日,我和丽娟准备给她办个小寿宴,您和嫂子一定要来啊。"临走时,建业诚恳地说。
"一定,一定。"我点头答应。
送走建业和丽娟后,我和淑芬商量了一下,决定拿出积蓄,给母亲买个新衣服作为生日礼物。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,但我想让她知道,儿子并没有忘记她。
三天后,我再次来到老家,给母亲带了一件新棉袄。这是我特意去百货大楼挑的,颜色喜庆,做工精细,比她那件旧棉袄好多了。

"妈,对不起,儿子能力有限。"我低声说,把棉袄递给她。
母亲盯着我看了许久,眼中的怒气渐渐散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了然和愧疚。她接过棉袄,抚摸着柔软的面料,眼圈红了。
"海子,你这孩子,花这冤枉钱干嘛?"母亲嘴上嫌弃,却迫不及待地试穿起来。
"妈,我知道您心疼建业,他确实是个好孩子。当年要不是他帮忙,您那病可不好说。"我坐在母亲身边,轻声说道。
母亲穿好棉袄,在镜子前转了一圈,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然后她转过身,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。
"海子,妈不是怪你,妈是心疼你......"她的声音哽咽了,"这些年你在外面打拼,妈知道不容易。只是你难得回来一次,妈想多看看你,多说说话。"
我突然明白了,母亲对我的责备,不过是想让我多陪陪她。年迈的老人,最怕的不是贫穷,而是孤独。
"妈,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"我承诺道。
"行,你有空就回来。对了,你闺女最近学习咋样?"母亲话锋一转,问起了孙女。
我们坐在炕头上,聊起家长里短。母亲给我讲邻居家的儿子如何孝顺,隔壁老张家的闺女如何有出息。我给母亲讲女儿在学校的趣事,淑芬工作上的变化。
不知不觉,天色已晚。母亲起身去厨房,说要给我做顿饭。我跟在后面,看着她忙碌的背影,心中既心疼又愧疚。
灶台上,母亲麻利地切着菜,锅里的热气腾腾升起,熟悉的香味弥漫开来。这是记忆中的味道,是家的味道。

吃饭的时候,母亲夹了一块最大的红烧肉放在我碗里:"海子,多吃点,瞧你瘦的。"
我嚼着那块肉,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些年,我总是忙于生计,忽略了最简单的亲情。而母亲,永远把最好的留给儿女。
"妈,下个月您生日,我和淑芬带着闺女一起来给您过。"我说。
母亲的眼睛亮了起来:"真的?你闺女能回来?"
"嗯,到时候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给您过个生日。"我保证道。
临走时,母亲一直送到村口,叮嘱我路上小心。
"妈,您回去吧,天冷。"我劝道。
"没事,多站会儿,看着你走远了我再回去。"母亲固执地说。
我转身离去,走了几步又回头,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,瘦小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。忽然,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:亲情从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,它是心与心的相互理解与牵挂。
回到家,淑芬正在阳台上晾衣服。看见我回来,她笑着说:"怎么样,跟妈谈好了?"
我点点头,帮她一起晾衣服:"嗯,下个月她生日,咱们一家人去给她过。"
淑芬欣然同意:"好啊,我给妈做她最爱吃的鱼香肉丝。"
晚上,女儿打来电话,说学校的交流项目很顺利,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我告诉她奶奶的生日,她开心地说一定会回来。
挂了电话,我坐在窗前,望着远处的灯火。这座城市,见证了我的苦难与成长,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,洒下一片清辉。我想起那个生锈的自行车铃铛,想起母亲穿新棉袄时的笑容,想起淑芬为我撑伞的样子。

生活不易,但爱让我们有力量继续前行。不管经历多少风雨,家永远是避风的港湾,而家人之间的理解,是渡过一切难关最珍贵的礼物。
窗前的月光如水,照在我的脸上,也照在我的心里。此刻,我感到无比踏实和安宁。尽管未来依然充满挑战,但有了家人的爱和支持,我不再感到孤单和恐惧。
离家的礼,不在多少,而在真心。